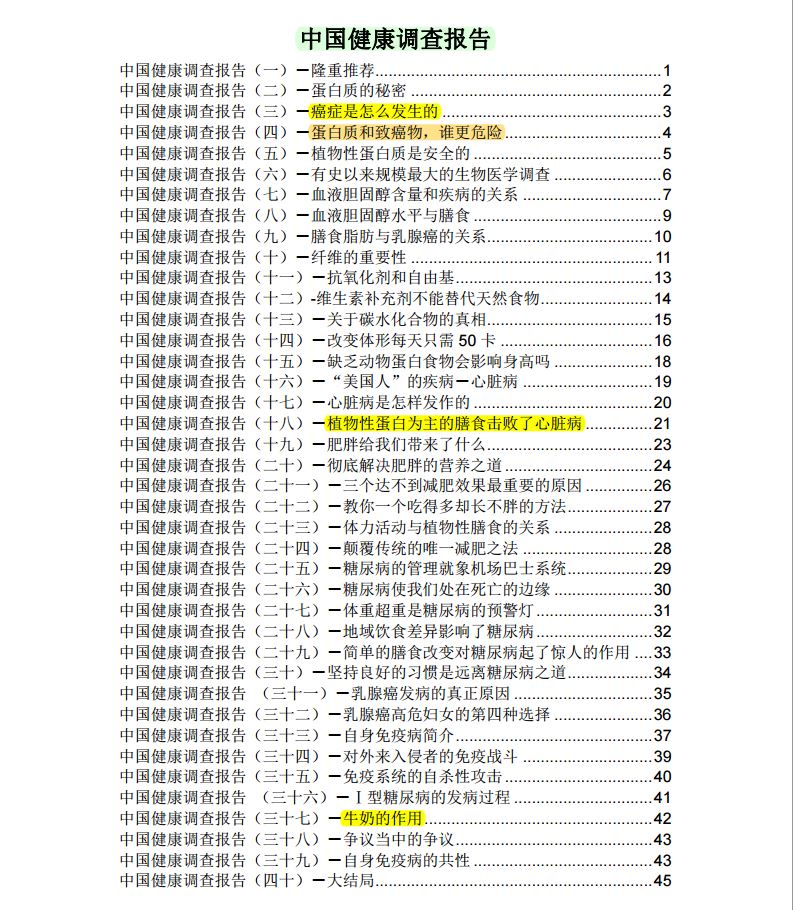严歌苓:关于母亲的两篇文章 (转载)
![]()
母亲与小鱼
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。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。那些修长的手指,那个略驼的背,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,后来都是哥哥的了。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。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。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。连母亲的歌喉、美貌,都险些被他忽略掉。母亲那时包了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,风头足极了,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,被她编成这样,弄成那样,什么服饰都不用,却冠冕似的华丽。十八岁的母亲,眼睛骄傲天真,却是有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是我的父亲。一天她忽然对他说:“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?”
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,在乐队拉小提琴,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。有时来了外国人,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。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。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,脸红了,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。
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,夹了一张小纸签:“我要嫁给你!”
她就真嫁给了他。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,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,胆怯,又有点拙劣。她把两岁的我抱着,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,在房里踱步。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,拍着我,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《摇篮曲》,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。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,眼神不在我身上。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。
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、认同。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“哆、来、咪”。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,右手拈一枝笔,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,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。要么,她大声朗读普希金,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,抬头去找这个声音,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,对她一笑。
她拿这一笑去维持后来的几天、几年,抑或半辈子的生活,维持那些没有钱,也没有尊严的日子——都知道那段日子叫“文革”。父亲的薪水没了,叫“冻结”。妈妈早已不上舞台,身段粗壮得飞快,坐在一张小竹凳上,“吱呀”着它,一晚上都在桌子上剖小鱼。她警告我们: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,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“劳动改造”一年没音信的父亲。
几条小鱼被串起来,用盐轻腌过,吊在屋檐下晾。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,妈妈在锅里放一点油,倒油之后,她的舌头儿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,抹布一样。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,她才来煎这些小鱼。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,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,起身站在厨房门口。
“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!”她发现我们,难为情地红了脸,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。
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。我们明白那种酥、脆连骨头都可口。然而我们只有嗅嗅、看着,一口一口地咽口水。
父亲回来后,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,说,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。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。看得出,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。她诱导他讲种种事,诱导他讲到吃,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。几年中,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,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。妈妈围绕着父亲,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。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像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。
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。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、猎装、皮夹克,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。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,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。
一天,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,从北京寄来的。他对我说:“是写给我们俩的。完了,他要和妈妈离婚了。”
信便是这个目的,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,放弃他,成全他“真正的爱情”。他说,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。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。他只是在熬,熬到我们大起来,他好有写这封信的一天。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,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。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?
许多天才商量好,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。她读完它,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。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,终于能歇口气了。
她看看我们兄妹,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,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: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,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,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。
这一夜,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“吱呀”声,听上去它要散架了。第二天一早,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。
父亲从此没回家。一天妈妈对我说:“我的探亲假到了。”
我问她去探谁。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,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。
“去探你爸爸呀。”她瞪我一眼,像说:这还用问?!
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。我们都成年了,也都不再缺吃的,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。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,“叫她别弄了!”他说:“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?”
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。我并且陪她上了“探亲”的路,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。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。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,妈妈说就暂时凑合,等找到父亲……心里作痛: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?
四月,杭州雨特稠。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。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,他已离开了杭州,相信他不是存心的,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,绝对无法追踪下去。我对妈说:冒雨游一遍西湖,就乘火车回家。
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。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,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,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:“邻居、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,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……”她想造一个幻觉,首先是让自己,其次让所有邻居、朋友相信:丈夫还是她的,起码眼下是的;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,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。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,或者,是被冷遇逐回的。
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。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,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,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。
父亲再婚后很幸福。妈妈见我就问:“她会做菜吧?”我当然明白“她”指谁,我说:“做得很好。爸爸也戒烟了……”她赶紧垂下头走开,不敢再听。
临回北京,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。竹凳也上了岁数,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。还是一堆小鱼儿,我不阻止她,懒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。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桩事了。竹像疼一样“吱呀”着,她说,再有场“文革”就好了,你爸又被罚到乡下,低人九等,就没有女人要他了,只有我才要他。她不敢抬头看我,怕我看见她眼里那片无救的天真,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。
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。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,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。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,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。他瞪了它一会儿,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,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。
这天父亲醉倒,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,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。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,我自然吞声。继母美丽的眼里,全是理解,全是理解……
失落的版图
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,竟是母亲的葬礼。
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,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,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“站立午餐”,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。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,一把抓起电话的。因为是心血来潮,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,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;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,更物质些(Physical),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,又多出一维空间。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。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,早已不必经过大脑,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。
三月的那个下午(正是祖国的清晨)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。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,电话铃一响,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。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,守候我的电话。自我远嫁,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。有时我连个“喂”都来不及招呼,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:“嘿,女儿!妈妈就知道是你。”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,事情已大不寻常了。我劈头就问:“妈妈呢?”继父没直接回答,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。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,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,问我先生的健康。我一字未答,等他圈子兜完,我仍是那句:“妈妈呢?”
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,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。他接着告诉我,妈妈胃癌已是晚期。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过程时,我重复地对自己说: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,但最终总要醒来,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。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,告诉我,我只是让梦魇所陷。却是没有一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。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。
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,一副爽脾气,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?每次回去探望她,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(扛起、背起)我的所有行囊,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,我却甩着两只空手,不断恳求她慢些走,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。她根本不理我,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,浑身没三两力气。有时我会跟她叫嚷:“妈妈,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,让你老太太当挑夫,会说这个女儿真够‘孝顺’的!”她仍是不理会,只是像一辆坦克一般闯去。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?
几天后我到了上海,再乘火车到南京。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。在我到达之前,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。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。正如二十年前,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,他们的婚姻该解体。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,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,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。
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,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,而不是妈妈。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,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。我一句也没听进去,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,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:妈妈应该知道真相;妈妈有权利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。我想,有我在她身边,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。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,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,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。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,话都排好了在舌尖上。
进病房时,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,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。我叫了一声“妈妈”,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。妈妈眼中,那等电话的等,等信的等,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,此刻全聚集在那儿……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,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,张向我,叫一声:“女儿!”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。我走上去,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。我那天在她病房里耽了六个小时,那句最难启齿的话,忽而在我喉口,忽而又退缩回心头。我想,我们将实情瞒着她,其实不是为她好,而是为我们自己好,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。在伪造的好气氛中,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,要好处得多。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,还去串通主治医生,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。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,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。南京三月的春意,是潮冷的,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。妈妈说:“女儿,妈妈得的是癌症,你知道吗?”
我瞠目看着她,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,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。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。我说:“别瞎猜。不是的,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。”妈妈看着我,有泪在我眼中烧灼。她笑了一下,带出一口叹息,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,就是要我同她一块承受这份真实;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,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,靠着谎言,混一天是一天。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。我眼泪再也噙不住,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,说:“好好,不是就不是!”这种时候,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,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。
这天以后,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,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。看妈妈吃饭,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。她是吃给我看的,机械地咀嚼,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存在了;再别出心裁的菜肴,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。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。妈妈却还总说:“嗯,好吃!闻起来就香!”当然,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。我跨了重洋归来,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式,一些失传的,一些刁钻的,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,她即使再难下咽,也领我一份心的。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。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,大声哈哈道:“妈妈,你今天气色特好耶!”她总是领情地一句:“是吧,我也觉得不错。”
第二次化疗后,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,似败草一样。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,演《雷雨》中的四凤,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。那样活的一根辫子,一甩一挥都是生命。话题就从头发开端,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,讲到得意时,她是完全康复了。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,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,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,又圆了。妈妈是好看的,年轻时更是,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,似乎什么都有过,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。
五月份,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,处理一些事务。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。临走前的晚上,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。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。她讲得很仔细,一个细节也不滑过。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,当护士告诉她“是个女儿”时,她从产床上窜起,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:“谢谢!谢谢!”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。
我没想到,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。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。
八月初,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,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。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,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。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,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。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,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。刚在旅馆下榻,我便拨了电话,通报我的到达。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:“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。”
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。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,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。我什么也没说,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,血尚要一会才会流出来,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迫上我的知觉。我一再问自己: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?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?我是什么人?住在这空寂的旅馆,走出去,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。
我哭不出来。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,坐了不知多久。大约是十二点多了,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,躺在床上,等着痛楚迫上来,等着眼泪追上来。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,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。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。我无梦无眠亦无思。没有了母亲,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,从此是缺了一块的。
五点钟,我起来,拨通了美国的长途,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。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,只知道讲得很长,抽泣使句子断裂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,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。我坐在那儿,心里白茫茫的,眼睛不大眨,也不大转动。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,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。我没了妈妈,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。
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。只有一小时,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。我临时写了悼词,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,只以满腹遗憾,通体悲伤,将全文凝聚起来。我仅念了第一句:“亲爱的妈妈,我回来了,不过已太迟了……”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“轰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四十岁的哥哥,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。
妈妈躺在鲜花丛里,嘴唇微启。哥哥告诉我,妈妈的最后一夜,一直在喃喃地说:“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。”
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。还叫着我的乳名,还口口声声叫我“好孩子”。有一刹那,错觉来了。似乎又是几十年前,我在后台,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、阿姨之间,寻找妈妈。总会有个人喊:“贾琳,你的千金在找你!”
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,门外的蝉声仍在嚎哭。我有一点明白,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。
✍: Guest
2016-06-14, 2910🔥, 0💬